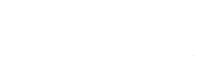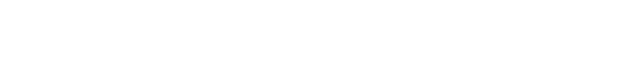迈向“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
孙 国 东*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如众所见,随着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出场及具有深厚左翼传统的法国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右转”压力,西方国家/文明历史性地开启了全球收缩的变局;同时,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与伊斯兰世界“去西方化”的文明扩张,又使得非西方世界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西方与非西方在世界结构之地位的此消彼长,已使此前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结构开始呈现出“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历史性变局,使诸多论者相信:当下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后西方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一种“新全球化”,特别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全球化”。 那么,究竟何为“新全球化”?一种教科书般的流行解释是,我们应超克“国族本位”(nation-obsessed)的全球化,提倡一种承诺了“世界主义”理想的全球化。换言之,我们要把“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political construction committed to publicity)扩展至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层面,也即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跨国家”(transnational)层面。这种规范性的世界主义想象,似乎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如果把西方主导的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的起点,那过去五百年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确是一种国族本位的全球化:无论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殖民体系的建立,还是“后殖民”时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对内民主、对外强权的政策取向,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族本位的。 就世界主义而言,其正当性毋庸置疑,有待检视的其实是其可行性问题:超越国族本位的世界主义何以可能?从传统中国的“大同”理想和“天下”观念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观念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千百年来无数圣贤都致力于超越国家的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想象,但时至今日为什么它们仍然只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这其中的制约因素,其实更值得认真对待。 有两个经济和政治因素,首先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自16世纪以来,全球共同进入的“世界”,是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基础之上的“世界”。如果说,人类在16世纪以前就共同生活在“地球”(earth)上,但直到地理大发现后的16世纪以来,人类才共同迈入交往更为密切的“世界”(world)。而驱动地理大发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换言之,人类过去五百年所共同进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来的产物。借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的说法,这种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其实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其最脆弱的历史时期把“资本主义”这个魔鬼从魔瓶中放出来的结果,即是全球范围“市场脱嵌于社会”(卡尔·波兰尼语)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抵制的意识形态,更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处境。然而,对全球化来说,资本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资本主义无国界的逐利取向固然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展开提供了经济条件,但建立在这种逐利取向之上对他国人民的掠夺、对本国底层社会成员(特别是无产者)的剥削等质野化特质,亦为我们从道德上驯服全球化提供了经济障碍。正是为了超越这种障碍,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试图以超越国界(国际主义)的阶级斗争,反抗全球资本主义对边缘国家和底层无产者的掠夺。然而,随着二战(特别是“冷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经济全球化全面扩展开来,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理想仍是镜花水月:毋宁说,“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更为现实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对倡导世界主义的“新全球化”来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根本挑战:如何在世界结构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形成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的有产阶层与无产阶层之间,实现基本的分配正义? 其二,自17世纪以来,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国家成为世界结构的基本单位。人类共同进入的“世界”,不仅是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基础之上,而且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亦开始建立在以拥有平等主权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万国体系”基础之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仅确立了民族国家作为全球资源竞争基本单位的合法地位,而且其所形成的“万国体系”亦在整个世界形成了资源争夺和政治认同的“国家之墙”。无论是重商主义时代(16-18世纪)西方国家之间的资源争夺,还是全球殖民体系时期(19世纪到二战前)西方对非西方国家的全球殖民,乃至二战后“后殖民主义”时代非西方各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尽管它们促使世界结构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由民族国家形成的“国家之墙”非但没有消除,抑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亦无消除的迹象和可能。对倡导世界主义的“新全球化”来说,万国体系的存在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根本挑战:如何使世界主义超越历史形成的“国家之墙”?特别是,如何使世界主义超越更为内在、更具文化和政治认同基础的国族本位取向? 上述第一个要素,是左翼论者尤为关切的问题;其他主张世界主义的论者更关注第二个要素——他们之所以主张世界主义,恰恰主要针对国族本位。在他们论者看来,国族本位不足为惧:既然民族国家在根本上是政治建构的产物(血统论的原生性民族国家并不存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民族国家之上想象世界主义的政治建构?为什么“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只能止于民族国家这一层面?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回答这一问题。在此,我拟从论者普遍忽视的人性视角稍作申论。 依我个人鄙见,人的情感有限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层面。所谓“人的情感有限性”,是说人的自然情感建立在人格化关系(伦理关系)基础之上,具有“爱有差等”的有限性。相较于与自己没有伦理关系的他人,人更容易对家人、朋友、同事、同胞等与自己有伦理关系的人产生感情。休谟最为深刻地洞察到了人的这种情感有限性,特别是其条件性。在他看来,爱可以单独地被另外一种关系——即我们自己和对象之间有关系——刺激起来。因此,我们自己与对象的关系越弱,其感情的程度亦会随之减弱。休谟的这种论说,与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的自然情感,以己为中心,随着与自己伦理关系的强弱而“愈推愈薄”,呈现出“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论者常常认为,这种“爱有差等”的差序格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事实上,“爱有差等”源于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情感有限性,因此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更确切地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格外呵护和关爱人的这种情感有限性——中国文化于此特质中瑕瑜互见,以至于不同论者之间的相互争辩(如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之间关于中国文化模式之优劣的争论),不过是因强调了不同面向而形成的“摘瑕”与“指瑜”的分野。 当然,人的自然情感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法产生超越于自然情感的情感,只不过——借用赵汀阳关于“自然情感”和“概念性情感”的区分——这种情感要靠一种“概念性情感”(如世界主义的情感)来维系。这种概念性情感,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具有“反自然”的内在脆弱性。吊诡的是,自国家产生以来,人类所有“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恰恰是要不断超克人的自然情感的有限性。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政治公职人员不能拥有家庭和私人财产的要求,到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希罗克洛斯(Hierocles)提出的“要恰当对待每个群体,把每一层圆圈都拉向圆心,满怀热情地把外围的圆转化为内层的圆”,从儒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理想,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愿景,他们都试图超越社会成员“爱有差等”的自然情感而推进“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然而,直到20世纪,“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方始以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成果,在民族国家层面普遍确立起来。以中国为例,尽管按照福山的说法,我们自秦代以来就建立了具有现代要素的国家,但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初步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我们遭遇更多的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在认同上的两极分化:普通民众“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但士大夫普遍念兹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跨国界文明归化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天下关怀,不屑于或不大认同“中夏安,远人服”这种带有政治现实主义意味的治国之道。 诸多倡导世界主义的论者乐观地相信:如果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不过是在政治共同体内部推进“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的产物,我们自然有理由期待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推进“致力于公共性的政治建构”——苟如此,“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便是计日可待的。然而,如果考虑到人的情感有限性,加之万国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构成了世界结构的基本格局,即使要提倡世界主义,它也只能是“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而不可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现代国家认同的普遍形成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其形成其实是长期以来历史积淀、政治博弈和社会演化共同作用的“未意图后果”(unintended result),即使在将来有可能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它也属于庄子所说的“来世不可待”的范畴。 所谓“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关涉三个互相关联的正义事项: 1.关涉世界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强制性要求。对国族本位的世界主义限制,遵循底线的“伤害原则”:国族本位的行动取向,不能以危害他国根本利益为代价,否则即受到基于世界主义的强制性干预。 2.关涉民族国家的基本行动取向:民族国家在自身的资源分配上应遵循“国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首先基本实现其内部的社会正义,那么承担促进全球正义的道德义务,就不是它的分内责任——在这方面,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同样适用于民族国家。 3.关涉世界主义对民族国家的范导性要求。各国在秉承“国民利益优先”原则促进本国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上,对促进全球正义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Responsibilities),即应当根据自己的历史条件、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等对促进全球正义承担力所能及的道德责任。 鉴于和平共处是万国体系得以存续的前提,“伤害原则”是最为基础的原则;鉴于民族国家仍是世界结构的基本单位,“国民利益优先原则”应当优先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由上述三个原则形成的“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充分尊重民族国家“国民利益优先”的行动取向,但主张以“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制,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其进行范导,从而形成了既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又承诺世界主义理想的均衡格局(三者的关系可见表1)。 表1:“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的规范性要求 正义事项 | 适用原则 | 规范性要求 | 原则属性 | 世界主义对民族国家行动取向的强制性要求 | 伤害原则 | 国族本位的行动取向不能危害他国的 根本利益 | 强制性原则 (底线原则) | 民族国家的 基本行动取向 | 国民利益优先原则 | 各国在自身的资源分配上要遵循“国民利益优先”的原则 | 基础性原则 | 世界主义对民族国家行动取向的范导性要求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 各国对于促进全球正义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范导性原则 |
* 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