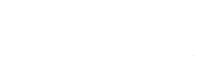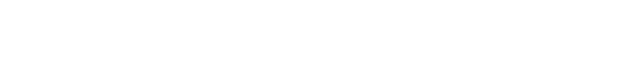文/柑草
按照习俗,已出嫁的闺女要在正月初二回娘家。 决定回家的头天晚上,我辗转难眠,百里之外的那个地方有让你拒之的伤痛也有让你奔赴的温情。 一直以来,距离成了归乡的绊脚石,尽管心心念,但不能说走就走。一年之中也只有中秋和春节会携夫带子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做短暂停留。 初二早早醒来,拉上孩子,装上礼物,出发。一个小时下高速再开一个小时的省道、乡道。 看似并不遥远,对我而言走得极为漫长。尤其是下了高速之后途经的每一个地区都让我觉得范围好大,许久才能到相邻那个。还有,归乡路上雷打不动发生在我身上的现象——年年回却年年“迷路”,总怀疑走的路不对,景不是印象中的景,物不是印象中的物,直到最为熟悉的乡村出现才能恍然大悟。 于是,孩子他爸总调侃我:“开车途中你不要瞎指挥,自己记不住还说别人错,你也就只能记住你们乡、你们村的路!” 那是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的地方,自然不会忘。
入村,南地一排排的新农村房子整齐划一,通往村庄的老桥已坍塌,新桥未修好,沟里填了土做临时通道。进村子中央,原本建在高高寨子上的学校早已“落地”,台阶下面原本空旷的操场早已码上密集的住宅,很多曾经熟悉的场景都已不复存在。 就连我们家也变了模样,十月份时把仅剩的堂屋也拆了,集中一个角落建了新房,余下的空地种上了瓜果蔬菜。 姑姑、表哥及堂妹一家都比我们早到。中午在叔叔家分成两桌就餐,虽是至亲,但孩子们相互间并不能熟识到叫出名字或称谓,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大团聚一次的孩子们怯生生地熟悉着、玩闹着。不仅是孩子,我们这一辈儿也很少话说,除了吃饭就是逗孩子,看着相互之间的生疏,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堵,我们都在努力往外走,没想到走得太远很难再回来。不得不感慨血缘又怎样,经常不见面依然会变陌生人。 就像在网上看到的那段话一样——没离开故乡时,故乡就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我们在画中嬉戏玩耍;当我们离开故乡时,故乡是一副挂起来的画,无论我们怎么走进,却始终隔着一层薄薄的纱…… 姑姑和表哥坐上车走后,妈妈跟我商量:“你晚会儿再走吧,你姐(大姨的女儿)前段时间做了手术,我带你去看看她。”
记忆中,我小时候没少在大姨家住也没少去大姨家玩,可自从后来去外地上学、工作后只去过大姨家两三次。表姐虽然嫁到了我们村,但也只去过她家两三次。 到了表姐家,她的两个儿子已比我高,时间真是魔法师。姐姐一如既往喊我“妮儿”,正是那接连不断的话语中时不时迸出的“妮儿,你不知道……”瞬间把我拉回了小时候,想起那时在大姨家看熬糖、做糖块,听录音带、学唱歌,晚上在院子里扯着灯泡剥棉花壳…… 很多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幻觉”,儿时自己家的木栅栏、土坯墙,伙伴家的蓝瓦房、大长院,村东边的小河沟、碾麦场,上学路上各家各户砌得有棱有角的粪堆、草垛等等都在眼前闪现,在这些场景中甚至仿佛会听到路过同学家时喊她“兰香、兰香”的声音,还能想起她家隔壁常挎着荆条编的篮子去校门口卖焦酥糖、花米团的老太太…… 太多变化来不及一一去观察,太多亲朋也来不及一一去看望,匆匆来匆匆去,能留下的能回味的已所剩无几。
转眼已是新年上班第一天,翻看朋友圈时发现家同样在百里外的朋友戏说春节假期还没有兔子尾巴长,也有朋友说过了个假年,的确,当“年味变了”成为话题时,“仪式感”这个词横空出世。 度娘说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确实,我们需要这些相聚、留影、串门儿、聊天的仪式,否则若干年后连回忆都找不到源素材。 归乡也是一种仪式,心之所向的地方因为你的回归而与其他日子所有不同,我们自己也因这种仪式而让漂泊歇歇脚。 |